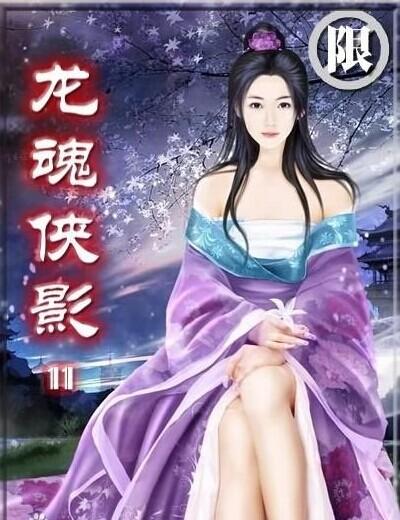趣书网>严党和清流党 > 第412章 俞大猷入赣下(第1页)
第412章 俞大猷入赣下(第1页)
兵部衙门内,陈恪提笔如刀,朱砂在宣纸上斩出凌厉笔画,一份《咨调浙直参将俞大猷猷进京备询东南防务及新式火药应用事》的文书顷刻而成。
他唤来堂吏,声音沉静无波:“即刻用印,归档。此乃兵部常规咨调,按甲字类留档备查。”
堂吏躬身领命,捧着那纸文书,如同捧着某种不容置疑的铁律。
陈恪行事,向来如此,无论内里乾坤如何翻覆,明面上的程序,必是严丝合缝,滴水不漏,让人寻不到一丝可供指摘的缝隙。
大步流星踏出兵部,陈恪并未耽搁,径直回府。
靖海伯府内,戚继光正襟危坐,眉宇间难掩焦灼。
见陈恪归来,他霍然起身,目光如炬。
“戚兄,成了!”陈恪嘴角扬起一丝如释重负的笑意,将精舍内惊心动魄的博弈、严嵩的狼狈闯宫、嘉靖的最终决断,删繁就简,只拣最紧要的结果道出。
“陛下圣明,已明旨俞将军无罪,官复原职,授‘剿倭总兵官’,即刻领军入赣,荡平倭寇!戴罪立功,不过是给某些人留个台阶罢了。”
戚继光闻言,紧绷的身躯骤然松弛,一股滚烫的热流直冲胸臆,虎目之中竟隐有水光闪动。
他猛地抱拳,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微颤:“子恒!大恩不言谢!俞兄他……他这条命,是你从鬼门关前硬生生拽回来的!”
狂喜之余,一个念头如同磐石般在他心底悄然生根——眼前这位年轻的靖海伯,不仅智计群,圣眷优渥,更难得的是这份为袍泽不惜涉险的赤忱!
这棵大树,他戚继光靠定了!未来若有风波,此人便是他戚家军最大的依仗!
“自家兄弟,何须言谢?”陈恪摆摆手,目光扫过窗外天色,“俞兄押解队伍,今日午后便至京郊。我已命厨房备下酒菜,你我这就出城迎他!这京城的诏狱大门,他不必进了!”
不多时,靖海伯府侧门洞开。
陈恪与戚继光翻身上马,身后亲兵抬着食盒酒坛紧随。
十余骑快马如离弦之箭,踏碎京郊官道上的薄霜,直扑城外十里长亭方向。
寒风凛冽,铅云低垂。
一行人勒马于官道旁一处视野开阔的土坡上,极目远眺。
不多时,官道尽头烟尘微起,几骑锦衣卫缇缇骑押着一辆囚车,在萧瑟的寒风中缓缓行来。
囚车木栅内,一个魁梧的身影披枷带锁,正是俞大猷!
虽身陷囹圄,脊梁却依旧挺得笔直,只是那饱经风霜的脸上,刻满了长途颠簸的疲惫与一丝不甘的沉郁。
陈恪眼神一凝,双腿一夹马腹,当先冲下土坡。
戚继光紧随其后,一众亲卫如雁翅排开,瞬间拦在官道中央。
“吁——!”押解的锦衣卫小旗官勒住缰绳,看清来人,脸上闪过一丝惊讶,随即翻身下马,快步上前,抱拳行礼:“卑职锦衣卫小旗邓福,参见靖海伯!”
陈恪端坐马上,目光如电扫过囚车,脸上瞬间罩上一层寒霜,声音冷冽如刀:“邓福!皇上是召俞将军进京回话,咨询军务!谁给你们的胆子,竟敢锁链加身,视朝廷大将如囚徒?!还不开枷放人!”
邓福心头一凛,额角瞬间渗出冷汗。
他久在锦衣卫当差,深知这位靖海伯的分量,更明白此事水深。
他不敢怠慢,一边示意手下开锁,一边凑近陈恪马前,压低声音,带着几分惶恐与无奈:“伯爷息怒!这……这非卑职之意,是……是上面的意思……”
他话未说完,便被陈恪抬手打断。
“什么上面下面!?”陈恪嘴角勾起一丝冷峭的弧度,声音陡然拔高,清晰得如同金玉交击,响彻旷野,“俞大猷接旨!”
囚车木栅刚被打开,俞大猷拖着沉重的镣铐踉跄而出,闻声浑身一震,毫不犹豫地推金山倒玉柱般跪倒在冰冷的官道上,头颅深深埋下:“罪将俞大猷,恭聆圣谕!”
陈恪展开早已备好的圣旨卷轴,朗声宣读:“奉天承运咨尔浙直参将俞大猷,前虽有疏失之议,然念其久历戎行,素有战功。今赣地倭患方炽,黎民倒悬,特授尔‘剿倭总兵官’,节制江西境内兵马,即刻率本部驰援,荡平倭寇!戴罪立功,以观后效!钦此!”
旨意虽未明言“无罪”,但“素有战功”、“特授总兵”、“节制兵马”等词,已将这“戴罪立功”的实质昭然若揭!
尤其是“率本部驰援”,更是直接点明了俞大猷的清白——若真是纵敌之将,岂能再统旧部?
俞大猷猛地抬头,眼中爆出难以置信的光芒,随即化为巨大的狂喜与激动!
他看到了陈恪身后,那个同样激动得眼眶红的戚继光!瞬间明白了是谁在圣前力挽狂澜!
他喉头滚动,满腔感激几乎要脱口而出:“伯爷!末将……”
“还不快谢恩!”陈恪厉声喝断,目光锐利如刀,扫过一旁垂手肃立的锦衣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