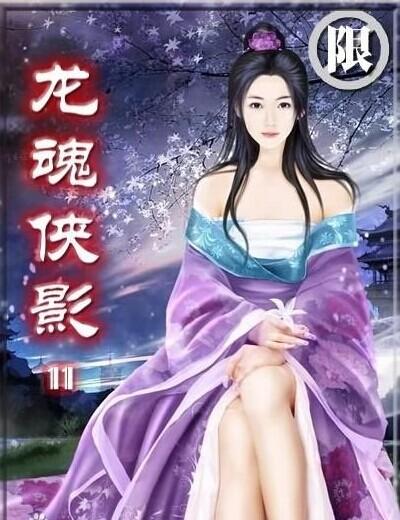趣书网>严党和清流党 > 第413章 狼烟骤起一(第1页)
第413章 狼烟骤起一(第1页)
俞大猷的风波,并未因其领军星夜驰援江西而彻底平息。
京城这潭深水,看似涟漪散去,实则暗流涌动更甚。
辅严嵩,这位深谙权术的老狐狸,比任何人都清楚“善后”的重要性。
他深知,俞大猷虽脱险,但其获释的“功劳”归属,却直接影响着远在东南的胡宗宪心中那杆秤的倾斜。
胡宗宪不仅是严党在东南的擎天柱,更是维系严家权势于东南财赋、兵权命脉的关键人物。
俞大猷作为胡宗宪的心腹爱将,某种程度上能左右胡宗宪的忠诚度。
于是,一场无形的舆论战悄然在京城展开。
很快,市井坊间、茶楼酒肆,乃至官员私下聚会的雅间里,开始流传一个“感人至深”的故事:辅严阁老,虽缠绵病榻,闻听俞将军蒙冤,竟不顾病体沉重,强撑病躯,直闯西苑精舍,在御前涕泪俱下,力陈俞将军之冤屈与功绩,甚至不惜以老迈之躯跪地泣血恳求,最终才打动了圣心,使得陛下收回成命,俞将军得以戴罪立功。
故事细节丰富,绘声绘色,尤其强调严阁老如何“拼了老命”、“不顾一切”地保下了俞大猷。
更有“知情人士”信誓旦旦地佐证,称亲眼目睹严阁老被搀扶出精舍时,脸色灰败,几近虚脱,足见其“赤胆忠心”与“爱才如命”。
这套说辞,经由严党门生故吏、依附官员之口不断传播、润色,其可信度在特定圈层内迅攀升。
与此同时,兵部衙门内,另一种声音也在悄然流出。
靖海伯陈恪在圣前据理力争,剖析利害,力证俞大猷非但无罪反而有功,并最终提出“戴罪立功、领军入赣”的务实之策,才是真正化解僵局、保全良将的关键。
这份说法,虽不如严党故事那般煽情,却更符合逻辑与部分朝臣对陈恪行事风格的认知,尤其是在兵部内部和陈恪亲近的官员圈子里,此论调颇有市场。
一时间,京城舆论场形成了奇特的“双峰并峙”。
一派感念严阁老“舍命相救”的恩德,一派推崇靖海伯“深明大义”、“智勇双全”的担当。
双方各执一词,谁也说服不了谁,争论往往无疾而终,却将俞大猷事件的余波持续扩散。
在信息传递缓慢、官方渠道高度垄断的古代社会,京城作为帝国心脏,其舆论风向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。
这里的流言蜚语、官员动向、政策风声,会通过塘报系统、官员家书、往来商旅、驿站传递等多种渠道,以惊人的度向四方扩散。
封疆大吏、地方官员乃至士绅阶层,无不时刻关注着京城的“风声”。
一则精心炮制的“佳话”,不仅能塑造个人形象、巩固政治同盟,更能深远地影响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权力格局的判断和站队。
严嵩深谙此道,他不在意京城内部的争论结果,他在意的是这则“拼死救俞”的故事,能否完整、及时地传到胡宗宪耳中。
他要让胡宗宪知道,为了保全他麾下的大将,他这位恩师在京城是如何“殚精竭虑”、“不顾生死”地周旋。
这份“恩情”,是维系胡宗宪忠诚的无形枷锁,其价值远俞大猷本人。
严嵩的算计精准而深远。
果然,不久后便有密报传来,胡宗宪在东南闻听此事后,沉默良久,最终对着京城方向深深一揖,并亲笔修书一封,遣心腹快马加鞭送入严府,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恩师“再造之恩”的感激涕零与“粉身碎骨难报万一”的效忠誓言。
严嵩看着这封言辞恳切的信,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、疲惫的笑意。东南的棋,暂时稳住了。
————
时间在看似平静中悄然流逝。
戚继光在陈恪的不断挽留下,在京城盘桓了两日。
他与陈恪秉烛夜谈,从东南倭情到练兵心得,从朝堂纷争到未来抱负,无所不及。
临行前,戚继光郑重地将自己数卷亲笔绘制的阵法图、练兵心得手札赠予陈恪。
这些并非泛泛之谈,而是戚继光能在东南屡建奇功的核心机密,凝聚着戚继光对倭寇战法的深刻理解。
“子恒,此乃戚某多年微末心得,或于子恒练兵强军有所裨益。东南局势未靖,戚某不敢久留,就此拜别!”
戚继光抱拳,眼中满是诚挚与托付。
陈恪郑重接过,深知这些凝结着实战经验的册子价值连城:“元敬兄厚赠,恪感激不尽!东南海疆,赖兄与俞兄砥柱中流,万望珍重!他日扫清倭氛,再与兄痛饮!”
两人在靖海伯府门前拱手作别,戚继光翻身上马,带着陈恪的期许与对东南局势的隐忧,绝尘而去,身影很快消失在官道烟尘中。
送走戚继光后,陈恪的生活似乎重归平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