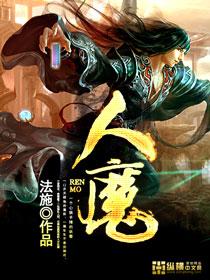趣书网>天幕在哪看 > 第41章 从速胜到堑壕3(第1页)
第41章 从速胜到堑壕3(第1页)
天幕的光芒,冰冷地照亮了欧洲1914年6月26日晚上整10时的夜晚,也照亮了天幕上泥泞、血腥、令人窒息的堑壕。
这光芒穿透了宫殿的厚墙和府邸的窗帘,同样也洒在伦敦拥挤的咖啡馆、巴黎烟雾缭绕的小酒馆、柏林路灯昏暗的街头。
伦敦,皮卡迪利广场附近一家名为“老橡木桶”的咖啡馆里,挤满了观看天幕的人群。
当画面切换到埃纳河进攻的惨败,士兵在机枪扫射下如麦秆般倒下时——
女招待手中的托盘“哐当”一声砸在地上,热咖啡溅了一地,她却浑然不觉,只是捂着嘴,泪水无声地涌出。
角落里,一个戴着圆顶礼帽、胸前别着和平协会徽章的老绅士,颤抖着手指着天幕上蜷缩在泥水里的年轻士兵,声音嘶哑地对同桌人说:
“看看!看看那些孩子!他们本该在农场、在工厂、在学校!现在却像老鼠一样泡在烂泥里等死!为了什么?为了国王和国家?还是为了那些坐在宫殿里抽雪茄的大人物们的野心?”
周围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泣和愤怒的低语。
巴黎,塞纳河左岸一间普通公寓里。
面包师的妻子玛德琳死死抓住丈夫的胳膊,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。
天幕上,一个年轻的法国兵徒劳地用一把豁口的铁锹在泥浆里挖着,雨水顺着他苍白的脸流下,混合着不知是泪水还是泥水。
“让…让是不是也在挖这样的沟?”
玛德琳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,她的儿子让,就在北边的部队里。
“上帝啊,这哪里是打仗…这分明是活埋!”
--
柏林,菩提树下大街。
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的历史学教授,刚结束一场关于“德意志文明优越性”的沙龙讲座,此刻却僵立在街头,失魂落魄地看着天幕。
画面中,一个德军士兵蜷缩在积水的战壕底部,怀里抱着一封被雨水浸透的信,眼神空洞地望着头顶铁丝网外灰蒙蒙的天空。
那士兵枯瘦的手上沾满泥污,像老树的根。
教授喃喃自语,声音轻得只有自己能听见:“铁与血…这就是铁与血的代价?我们引以为傲的士兵…在烂泥里腐烂?”
一丝动摇和深切的同情,第一次压过了他心中狂热的民族主义。
他身边匆匆走过的市民,许多人也停下了脚步,脸上不再是战争初期的狂热,而是震惊、茫然,甚至…恐惧。
一种超越了国界的、对同类悲惨处境的同情,在冰冷的夜空中无声弥漫。
--
然而,这弥漫于市井的悲鸣与同情,却无法穿透权力核心那冰冷厚重的墙壁。
伦敦,白金汉宫。乔治五世国王的目光从天幕上泥泞的堑壕移开,落回室内烟雾缭绕的“战场”。
他刚才那句“优势在于我们”的回音似乎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