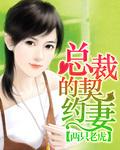趣书网>左传游记有哪些特色 > 第107章 光荣参军表文公第四年(第2页)
第107章 光荣参军表文公第四年(第2页)
唐朝建立后,府兵制臻于完善。全国设立折冲府600余处,以"内重外轻"策略拱卫京师,府兵需通过严格的"材力"考核,不仅要求善骑射、通兵法,还需具备良好的家世背景。府兵随身携带的鱼符与折冲府调兵凭证相契合,这种严密的管理制度确保了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掌控。唐太宗李世民以"自古皆贵中华,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"的胸襟,吸纳突厥、契丹等少数民族将领,阿史那社尔、契苾何力等异族名将在唐朝军队中屡立战功,彰显出大唐海纳百川的军事用人之道。
这一时期,募兵制的萌芽与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兵役体系。唐玄宗时期,府兵制逐渐崩坏,取而代之的是"长征健儿"的募兵制度。这些职业军人由国家供给粮饷装备,长期戍守边疆,高仙芝、哥舒翰等名将麾下的安西、陇右军成为大唐对外扩张的精锐力量。安史之乱后,藩镇割据局面形成,地方节度使大量招募私兵,虽导致中央集权削弱,却也催生出如魏博牙兵等战斗力强悍的地方武装,展现出军事力量与地方势力的复杂博弈。
在文化领域,隋唐时期的文学艺术将参军报国的精神推向新的美学高度。边塞诗成为唐代诗歌的重要流派,王昌龄"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破楼兰终不还"的豪迈,王之涣"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"的苍凉,岑参"将军角弓不得控,都护铁衣冷难着"的写实,不仅描绘了戍边将士的艰苦生活,更抒发了他们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。阎立本《步辇图》中吐蕃使者朝见唐太宗的场景,以艺术形式展现军事威慑下的和平外交;昭陵六骏石刻则通过浮雕战马,纪念唐太宗征战四方的赫赫战功,将军事功绩升华为民族记忆的象征。与此同时,佛教的"护国"思想与儒家的"忠君报国"理念深度融合,为军人提供了更丰富的精神支撑,敦煌莫高窟中《张议潮统军出行图》的壁画,既展现了归义军收复河西的壮举,也蕴含着宗教对军事胜利的护佑祈愿。
到了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战乱年代,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,军事力量成为左右时局的决定性因素。这一时期,兵役制度在混乱中呈现出极端的实用性特征。各割据政权为维持统治,纷纷推行“黥面为兵”的强制征兵法,即在士兵脸上刺字以防逃亡,如后梁太祖朱温将招募的乡民脸上刺上“定霸都”字样,使士兵彻底沦为终身服役的战争工具。这种残酷手段虽确保了兵源稳定,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,引发底层民众对参军的恐惧与抵触。
藩镇势力的恶性膨胀,催生出“牙兵”这一特殊军事集团。他们作为节度使的亲兵卫队,享受优厚待遇却也骄横跋扈,动辄发动兵变废立主帅,形成“天子,兵强马壮者当为之,宁有种耶”的乱世法则。魏博牙兵历经数代割据,成为左右河朔局势的“定海神针”,但也因其恃功而骄加速了藩镇政权的衰亡。与此同时,沙陀族建立的后唐、后晋、后汉政权,将少数民族的军事传统与中原制度相融合,以骑兵优势纵横中原,展现出胡汉军事文化交融的独特景观。
文学艺术领域虽因战乱而发展受阻,但仍有作品深刻反映时代的军事特征。韦庄的《秦妇吟》以史诗般笔触描绘黄巢起义后的兵燹之祸,“内库烧为锦绣灰,天街踏尽公卿骨”的惨状,控诉了战争对文明的摧残;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虽以宴乐场景为主,却暗含南唐政权面对北方军事威胁时的焦虑与颓唐。而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雏形,已开始塑造忠勇报国的军人形象,为后世军事文学提供了丰富素材。
在军事思想层面,由于政权更迭频繁,军事家们更注重权谋与实用策略。冯道历仕四朝十君,其“但教方寸无诸恶,狼虎丛中也立身”的处世哲学,折射出乱世军人在道德与生存间的艰难抉择。此时的兵书多以总结实战经验为主,如《握奇经》注疏本强调灵活用兵,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,体现出军事理论从宏大战略向具体战术的转变。这一时期的参军报国观念,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被蒙上了浓重的现实功利色彩,既延续着传统的忠君思想,又因时局动荡而充满对个人命运的无奈与挣扎。
紧接着,到了辽宋夏金元时期,多元政权并立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特征,深刻重塑了参军报国的内涵与形式。契丹建立的辽朝推行"兵民合一"的部族军制,以"斡鲁朵"宫卫骑军为核心,兼具戍卫与征战职能,其"四时捺钵"制度将军事训练融入游牧生活,展现出独特的草原军事智慧。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则创设"擒生军",战时掠夺人口充实国力,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中对军人职责的详细规定,体现出军事制度的法典化进程。
北宋王朝吸取五代教训,实行"强干弱枝"策略,建立起庞大的禁军体系。赵匡胤通过"杯酒释兵权"收归武将权力,推行募兵制吸纳流民与灾民入伍,既缓解社会矛盾,又形成"养兵以自固"的军事传统。范仲淹戍守西北时改革军制,提出"屯田实边"之策,《渔家傲·秋思》中"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"的词句,道出了宋代军人报国与思乡的复杂情感。然而,过度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宋军战斗力疲软,与辽、西夏的长期对峙中屡处下风,催生了狄青、岳飞等力挽狂澜的军事将领,他们"精忠报国"的精神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。
金朝崛起后,女真族以"猛安谋克"制度组织军事力量,兼具行政、生产与军事职能,战时壮丁皆兵,战后解甲归田。金世宗时期推行"签军"制度,征调各族壮丁扩充军队,促进了民族间的军事融合。元朝建立后,构建起以蒙古军为核心、探马赤军为先锋、汉军与新附军为辅助的军事体系,"军户制"下士兵世代服役,自备装备粮草,形成严密的军事组织。元朝疆域辽阔,军队不仅承担征伐任务,还负责维护驿站交通、戍守边疆,马可·波罗笔下的元军骑兵,展现出强大的机动能力与征战韧性。
这一时期,军事文化呈现出多元碰撞的特征。辽代的《焚椒录》记录萧观音的军事谋略,展现女性在军事决策中的作用;南宋陈亮、叶适的事功学派,批判空谈心性,主张以军事改革振兴国家;元杂剧《单刀会》中关羽的忠义形象,既体现儒家思想,又融入民间对军人品格的推崇。同时,火药武器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,改变了传统军事格局,南宋的突火枪、元朝的火炮,标志着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的过渡,参军报国的技能要求与战略思维随之发生深刻变革。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军事实践,不仅是各政权生存竞争的体现,更是不同民族军事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阶段,为中国军事史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不久之后,到了明清时期,中国的军事体系在传统与变革的激荡中迎来新的转折。明朝建立伊始,朱元璋借鉴历代兵制,创设卫所制度,全国设立卫、所两级军事编制,士兵"三分守城,七分屯田",形成自给自足的军事体系。卫所军士携带家属定居驻地,户籍世袭,既保障了稳定兵源,又促进了边疆开发。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,其水师不仅彰显大明国威,更将军事力量与和平外交有机结合,使参军报国的内涵延伸至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繁荣。
然而,随着时间推移,卫所制逐渐僵化。明中期后,土地兼并严重,军士逃亡现象频发,戚继光、俞大猷等将领开始招募乡勇组建新军。戚继光在浙江招募的"戚家军",以义乌矿工、农民为主体,采用严格的训练方法和鸳鸯阵战术,成为抗击倭寇的中坚力量。这些募兵制下的军队,打破世袭局限,以实战能力为选拔标准,"封侯非我意,但愿海波平"的誓言,展现出军人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崇高境界。同时,火器在明代军队中的大规模应用,催生了神机营等专业化火器部队,《武备志》中对各类火器的详细记载,标志着军事技术与战术理论的重大突破。
清朝初期,以八旗制度为核心构建军事体系。满洲八旗、蒙古八旗、汉军八旗构成清朝统治的军事支柱,旗人"出则为兵,入则为民",享有特殊政治地位。康熙帝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、抗击沙俄,八旗铁骑在维护国家统一中发挥关键作用。但随着承平日久,八旗兵逐渐腐化,乾隆后期不得不依赖绿营兵维持统治。晚清时期,内忧外患加剧,曾国藩创建湘军、李鸿章组建淮军,采用"兵为将有"的募兵原则,以地域、血缘为纽带凝聚军队。湘军"结硬寨,打呆仗"的战术,既传承传统军事智慧,又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展现出强大战斗力。
鸦片战争后,西方军事思想与技术的冲击促使中国军事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。洋务运动期间,清政府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,建立北洋水师等近代化海军,翻译《克虏伯炮说》等西方军事着作。甲午战败后,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,采用西式军制、训练方法和装备,从编制到战术全面向现代化转型。这一时期,参军报国的理念与救亡图存紧密相连,谭嗣同"我自横刀向天笑"的慷慨赴死,秋瑾"休言女子非英物"的巾帼豪情,将军人精神升华为民族觉醒的象征。文学领域,《官场现形记》对晚清军事腐败的批判,与《孽海花》中爱国志士的抗争描写,共同构成对军事变革的深刻反思,为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留下生动注脚。
而在欧洲各国,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,对于光荣参军护国的认识,便已深深植根于城邦文明与帝国扩张的土壤之中。古希腊城邦以公民兵制为基石,将军事义务与公民权利紧密捆绑。在雅典,凡年满18岁的公民皆需在军事训练所接受系统训练,战时自备武器组成重装步兵方阵。这种"全民皆兵"的制度下,参军不仅是保卫城邦的责任,更是获得政治参与权、彰显公民身份的必经之路。斯巴达更是将军事主义推向极致,男孩从7岁起便离开家庭,在严酷的军事训练中培养坚韧意志与集体荣誉感,"要么胜利归来,要么战死疆场"的信念,使参军护国成为斯巴达公民至高无上的荣耀。
在文学艺术领域,《荷马史诗》中阿喀琉斯为荣誉而战、赫克托耳为城邦献身的故事,塑造了古希腊军人的理想形象,这些英雄传说不仅是对战争的歌颂,更是对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礼赞。雅典卫城的浮雕、帕特农神庙的柱廊,常以战争胜利为主题,将军事功绩凝固为永恒的艺术丰碑。哲学家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构想的"护卫者"阶层,强调军人应兼具智慧与勇气,将参军的意义从单纯的武力对抗,提升到维护正义秩序的哲学高度。
古罗马的军事体系则随着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型不断演进。早期实行公民兵制,规定拥有一定财产的公民才有资格参军,军团士兵自备装备,通过战功获取土地与财富,这种制度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随着疆域扩张,马略改革推行募兵制,职业军人取代公民兵,军队职业化程度大幅提升。罗马军团严明的纪律、标准化的军事工程(如道路、营垒建设),以及"龟形盾牌阵"等战术创新,使其成为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。
在罗马文化中,军事荣耀被视为最高荣誉。凯旋门的建造、胜利女神像的雕塑,都是对军事成就的永恒纪念。诗人维吉尔在《埃涅阿斯纪》中,将罗马的军事扩张描绘为神授使命,赋予战争神圣色彩;历史学家李维在《罗马史》中,通过记述布匿战争等重大战役,宣扬罗马人的爱国精神与尚武传统。罗马法中对军人权利的保障、退役后的土地分配政策,进一步强化了参军护国的吸引力,使军事生涯成为公民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。这些早期实践,为欧洲军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,其蕴含的荣誉观念、公民责任与军事智慧,至今仍在西方军事思想中留下深刻印记。
紧接着,到了后来,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,欧洲的参军护国观念与制度在基督教信仰、骑士精神和封君封臣体系的交织影响下,呈现出全新的面貌。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,日耳曼部落的军事传统与罗马残余军事制度相融合,催生了以采邑制为基础的兵役体系。封臣们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(采邑),作为回报,需在战时率领装备精良的骑士参战,这种"以土地换军事服务"的模式,将参军行为转化为封建义务与荣誉的双重载体。
骑士阶层的崛起成为中世纪军事文化的核心。自公元8世纪查理·马特推行采邑改革后,骑士逐渐演变为职业战士,他们不仅需要掌握骑术、剑术等军事技能,更需遵循基督教教义与骑士精神准则。骑士精神强调"谦卑、荣誉、牺牲、英勇",将参军作战升华为扞卫宗教信仰、保护弱者的神圣使命。十字军东征时期,教会宣扬"为上帝而战可获救赎",成千上万的骑士响应号召,佩戴十字徽章奔赴圣地。《罗兰之歌》中罗兰骑士为守护查理曼帝国壮烈牺牲的故事,生动诠释了骑士对荣誉与忠诚的执着追求,成为中世纪参军报国精神的文学典范。
在军事制度层面,中世纪军队呈现出鲜明的等级特征。贵族骑士作为核心战力,身着锁子甲、手持长矛与盾牌,冲锋陷阵;普通步兵则由农民临时征召,承担后勤与辅助作战任务。随着战争规模扩大,雇佣军开始兴起,瑞士长矛兵、热那亚弩手等职业化部队以精湛技艺闻名,打破了传统封建兵役的局限。城堡建筑技术的发展,使军事防御体系发生革命性变化,星型要塞、护城河与箭塔构成的防御网络,重塑了战争形态,参军作战的技能需求从单纯的近身格斗扩展到攻城与防御技术。
在文化领域,宗教艺术与文学作品深刻影响着参军观念。教堂彩窗上描绘的圣乔治屠龙、圣马丁分袍等宗教故事,将军事勇气与基督教美德相融合;行吟诗人传唱的亚瑟王传奇,塑造了圆桌骑士的理想形象,使参军成为追求荣耀与爱情的浪漫选择。托马斯·阿奎那在《神学大全》中对"正义战争"理论的阐释,为中世纪战争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,认为符合宗教与伦理标准的军事行动是维护上帝秩序的必要手段。这些思想与实践,既延续了古典时期的军事荣誉传统,又赋予参军护国以强烈的宗教色彩与道德使命,构成了欧洲中世纪独特的军事文化图景。与此同时也为后来的新航路的开辟、文艺复兴运动、科学大发展、宗教改革运动、乃至是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工业革命,以及后来的各大战役与近现代两次世界大战的光荣参军制度,奠定了一定的“基石”与“基础”。
与此同时,在古印度,阿拉伯世界和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,对于光荣参军护国观念的研究应用与实践发展,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。
在古印度,参军护国的荣耀观念深深根植于种姓制度与宗教信仰之中。刹帝利阶层自诞生起便肩负起保卫国家、维护社会秩序的神圣使命,《摩奴法典》明文规定他们应精通兵法、英勇作战,其战功不仅关乎个人荣誉,更被视作维系宇宙秩序“达磨”的重要责任。孔雀王朝时期,阿育王以庞大的常备军开疆拓土,士兵们在战象与青铜兵器的轰鸣声中,将对王权的忠诚与对宗教护佑的笃信融为一体;笈多王朝的武士们则在征战中,以吠陀教的战争史诗为精神指引,将每次冲锋都化作对神明与家国的献祭,使参军护国成为神圣与世俗荣耀的双重象征。
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文化中,参军护国与伊斯兰教义紧密交织。“圣战”(吉哈德)概念既包含抵御外敌、保卫信仰家园的神圣使命,也蕴含着通过战斗传播教义、维护正义的精神内核。早期穆斯林战士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,为扞卫新生的伊斯兰社群而战,将战场视为通往天堂的试炼场,《古兰经》中“为主道而战者,你当以正信鼓舞他们”的训诫,激励着无数阿拉伯勇士奔赴战场。阿拔斯王朝时期,职业军队“马木留克”以精湛的骑射技艺和绝对忠诚闻名,他们不仅是国家的军事支柱,更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,在东征西讨中,将阿拉伯的智慧与信仰带往更广阔的疆域,参军护国由此升华为守护文明火种的崇高事业。
而在古埃及与非洲大陆传统文明,以及美洲的玛雅、阿兹特克与印加文明,对光荣参军卫国,似乎也有着很深刻的认知与理解。
在尼罗河畔,古埃及的参军护国理念深深烙印着太阳神崇拜的神秘色彩。法老被视作神明在人间的化身,士兵们坚信为法老而战即是为神明效力。新王国时期,图特摩斯三世建立起庞大的常备军,年轻战士们在卡纳克神庙前举行庄严的出征仪式,将荷鲁斯神的鹰徽纹在盾牌上,认为每一次挥剑都是在践行神谕。底比斯的军事学校中,教官们教授象形文字记载的古老兵法,让士兵们理解“保卫尼罗河沃土即是守护玛阿特(真理与秩序)”。拉美西斯二世时期,卡迭石战役的胜利纪念碑上,密密麻麻刻满士兵的名字,他们的英勇事迹随着尼罗河水的流淌,成为古埃及人世代传颂的参军荣耀。
在非洲大陆,部落文明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参军护国的意义。东非马赛族的战士“莫兰”自少年时期便开始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,他们以猎杀狮子证明勇气,将保卫部落畜群与领地视为神圣职责。战士们佩戴着象征力量的红玛瑙珠串,在草原上高唱战歌,用盾牌与长矛构建起抵御外敌的防线。西非的马里帝国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军团,曼萨·穆萨时期的战士们不仅精通骑射,还将经商贸易的智慧融入军事行动,在保卫商路的同时,将帝国的荣耀与文明传播四方。部落战士们坚信,自己的每一滴热血都将滋养脚下的土地,死后灵魂也将守护族群生生不息。
美洲的玛雅文明中,参军作战是贵族阶层获取政治地位与宗教威望的重要途径。城邦间频繁的战争促使玛雅青年以成为“阿哈尔”(勇士)为荣,他们在金字塔前举行“血祭仪式”,用放血的方式祈求神灵护佑胜利。玛雅战士身着精美的羽毛战衣,手持黑曜石刃的武器,在战场的呐喊声中,将俘虏献祭给雨神查克,认为这是维护宇宙平衡的必要牺牲。阿兹特克文明则将参军护国与“太阳崇拜”紧密相连,战士们相信为帝国而战能为太阳补充能量,延缓世界末日的到来。“雄鹰武士”与“美洲虎武士”是阿兹特克最精锐的力量,他们佩戴着象征力量的兽形头盔,在特诺奇蒂特兰的神庙前接受最高祭司的祝福,将征服其他城邦视为神圣使命。而印加帝国的“查查波亚”战士们,以安第斯山脉为天然屏障,用青铜兵器与坚韧意志保卫“太阳之子”的国度,他们修筑的军事要塞至今仍矗立在云端,诉说着参军卫国的不朽传奇。
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,除了中国以外,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,以及俄罗斯同样在光荣参军卫国价值认识领域,留下了独特印记。
在日本列岛,参军卫国的理念与武士道精神、神国思想深度融合。自平安时代起,以源平合战为代表的武士集团纷争中,武士们将"忠君报国"视为最高道德准则,其行为规范被编纂成《叶隐闻书》,书中"武士道,乃求死之道"的箴言,将赴死沙场升华为美学与信仰的终极追求。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等战国大名通过"兵农分离"制度建立职业化军队,士兵们在出征前参拜伊势神宫,将守护天皇与开疆拓土视为神道教"八纮一宇"理念的实践。江户时代,虽然进入和平时期,武士阶层仍通过《叶隐》《武道初心集》等典籍传承尚武精神,将日常的武艺修行等同于战场的忠诚,使参军卫国的信念渗透进日本文化血脉。
朝鲜半岛的参军文化则深深植根于儒家伦理与保家卫国的现实需求。新罗王朝时期,花郎道将佛教的慈悲、儒教的忠孝与道教的养生思想融为一体,培养出既能征战沙场又具文化修养的"花郎徒"。他们在《誓记石》前立下"事君以忠,事亲以孝"的誓言,将参军视为践行人伦道德的最高体现。李氏朝鲜建立后,朱子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,"精忠报国"的观念通过《经国大典》制度化。壬辰倭乱时期,朝鲜军民在"卫正斥邪"的旗帜下奋起抵抗,李舜臣等将领以"死即死耳,何惧之有"的壮语激励士卒,龟船舰队在鸣梁海战中重创日军,将参军卫国升华为扞卫文明存续的壮烈抗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