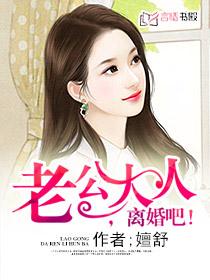趣书网>花屋湘军传奇 > 第94章 冰刃照芙蓉(第1页)
第94章 冰刃照芙蓉(第1页)
光绪十二年(1886年)的深秋,湘江的水流似乎也带上了一股从西北裹挟而来的粗粝与寒意。
一艘半旧的官船破开浑浊的水面,逆流而上,朝着长沙码头缓缓靠拢。
船头立着一个青年,身姿挺拔如岳麓山巅的劲松,正是东归的谭嗣同。
他身上的青布棉袍洗得有些白,浆洗得硬挺,却掩不住那宽厚肩膀和挺直脊梁勾勒出的力量轮廓。
三年的光阴,将那个曾带着京城贵胄子弟特有浮华印记的少年彻底淬炼。
新疆,刘锦棠大帅那风沙弥漫、号角连营的帐幕,成了他真正的熔炉。
白日里,他伏案于堆积如山的舆图、粮册、民情文牍之间,笔下流淌出关于屯田、水利、边贸的条陈,字字浸透着对那片辽阔疆土的洞察与忧思。
入夜,则是截然不同的世界,戈壁滩凛冽的寒风中,篝火噼啪作响,映照着汗流浃背的身影。
他随帐下那些百战余生的老兵习练刀法。西北的刀,厚重、直接、带着沙场喋血的狠戾。
从最初笨拙地挥舞那沉甸甸的环刀,到后来刀光泼洒如雪,能在十招之内让教授他的老哨官脱手认输,他的掌心磨破又结痂,厚厚的老茧无声诉说着无数个寒夜的砥砺。
刘锦棠那鹰隼般锐利的目光里,赞许日益浓厚。
临别时,大帅拍着他的肩,声音洪亮如擂鼓:“复生!好小子!是块真材实料!回关内去,大有可为!江苏那个富庶地界,老夫替你向朝廷争一争!”
这份赏识,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,是期许,更是鞭策。
船身微微一震,靠上了长沙麻石砌就的码头。
熟悉的乡音、湿润的空气、两岸熟悉的丘陵轮廓扑面而来,带着一种久违的温软,却也透着一丝陌生。
他深吸一口气,那气息里混杂着泥土、水腥和人烟的味道,与西北干燥清冽、带着铁锈和尘土气息的风截然不同。
他紧了紧肩上简单的行囊,那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,便是一柄用旧布仔细缠裹的环腰刀——刘锦棠所赠,刀身狭长微弧,吞口处磨损得厉害,却透着冷硬的幽光。
这柄刀,是他这三年脱胎换骨的见证。
归家数日,短暂的亲伦温暖之后,一种无形的沉闷便悄然围拢。
京城的旧友圈子,听闻他回来,帖子雪片般飞来。
宴席依旧设在最奢华的酒楼,雕梁画栋,丝竹绕耳。
席间觥筹交错,话题却总离不开京里新得了什么稀罕玩意儿,谁家戏班又出了个绝色的旦角,或者是哪位大人物的风流韵事。
那些华服包裹下的面孔,带着精致的笑容,眼神却空洞浮泛。
谭嗣同端坐其中,听着这些曾经熟悉无比、如今却显得格外遥远空洞的谈笑,只觉得杯中醇厚的陈酿也失了滋味,甚至隐隐泛起一丝苦涩。
他感觉自己像一株被移栽回温室的胡杨,周围的空气温暖湿润得让他有些窒息。
西北的烈日风沙、大漠孤烟、帐中烛火下与刘锦棠纵论边塞安危的激越、校场上刀锋破空的锐响……这些刻入骨髓的记忆,与眼前这浮华精致的场景格格不入。
他沉默地放下酒杯,目光投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,心底那股躁动越来越清晰——他要出去,离开这令人窒息的锦绣牢笼,去呼吸更广阔、更真实的天地气息。
几日后的清晨,他牵出家中一匹健硕的青骢马,只对老管家说了一句“去城外散散心,不必备饭”,便策马出了城门。
马蹄踏在郊外略显泥泞的土路上,出沉闷而规律的“哒哒”声。
深秋的湘地,寒意初透,田野间弥漫着收割后稻草焚烧的淡淡烟气和泥土的微腥。
远处的山峦在薄雾中起伏,勾勒出柔和的黛色轮廓。
这熟悉的南国景致,让他紧绷的心弦稍稍松弛。
他信马由缰,漫无目的,只想让这带着凉意的风,吹散心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郁结。